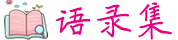梁鸿记得,以前,每天清晨6点,父亲就醒了,在院子里来回踱步。
穿着白衬衫,大声唱着戏文。

“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
“俺家住在河岸边,母生下多男并多女。
所生俺一女名叫凤莲。
早不幸,老母亲把命丧,撇下了俺父女,以打渔度过荒年。”
两年前,父亲去世了。她已经许久未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她把这段戏文写进《梁光正的光》这本小说里,让里面的主人公梁光正也天天清早唱起来。
父亲与梁光正,真实与虚构之间,总有一些言行的重叠,精神的交织。
两年来,梁鸿想一步步走近那道光,去感受光芒与背后的阴影,去理解散发光芒的那个人。
父亲与梁光正
梁鸿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她并不真的了解他。
“他一直是我的疑问。
而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梁鸿回忆了儿时和父亲见面的一幕。
那时候,河南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
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正在读中学的梁鸿要去镇上上课。
他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励志语录网 www.lz16.cn)
他朝她笑着,看着已经长到和他肩膀一样高的梁鸿,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
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
“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
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
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书中唯一真实的细节,就是白衬衫。
与梁鸿的父亲一样,梁光正也总喜欢穿着一件白衬衫。
他是个农民异类,不爱种地,整天穿着干净得耀眼的白衬衫;
他搞过“投机倒把”被当流窜犯关押过,偷过黄豆;
他一辈子都在创业,虽然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他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家庭所遭的罪也都因此而起。
村干部想引进项目收购村民土地。
梁光正认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更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就联合村民反对项目落地。
村里有人受欺负,他就带头帮人打官司,最后却败诉导致那家人倾家荡产。
他还是个渴望爱情的人。
在书中的开端,梁光正任性地拉着四个子女到处寻亲。
既要寻找久未联系的远亲、偶然间帮助过自己的陌生人,还要寻找多年未见的旧情人蛮子。
妻子生病七八年后,梁光正把遭受家暴差点送命的蛮子和儿子小峰救了出来,一起生活。
他的三个儿女在照顾时出现了失误,小峰被严重烫伤,蛮子就带着小峰离开了。
像月球表面一样的伤疤烙印在小峰身上,每个人心中都埋藏着深渊一般的痛苦。
梁光正生重病却吵着出院后,瞒着儿女,偷偷打电话叫多年不见的旧情人蛮子到家里见面。
蛮子到了,突然,梁光正伸手牢牢抓住了蛮子的乳房。
周围的人无论是震惊、羞愤还是不解,全都安静了下来,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梁光正和蛮子。
蛮子挣扎了几下,随后就抱着梁光正一直安慰说:“好了好了,别煎熬了。
都长大了,都成家了,你操心啥?
你该享福了。”
梁光正像小婴儿一样“吧嗒吧嗒”地使劲吮吸蛮子的乳房。
梁光正内心所承受的负担很重。
他一个人要养4个孩子,还要挣钱带常年瘫痪的妻子四处求医看病。
又不肯放弃人的尊严,抗争一切不公平的事情。
他一生都在渴望获得真正的感情,但在中年时代,他连一场完整的爱都不能实现。
“我想弥补他,或者让大家读到他内心丰富的感情。
对爱的要求,对子女的牵挂。”
在这一刹那,子女突然发现,自己总是把梁光正作为父亲来看。
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原来我们的存在也妨碍了梁光正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很多媒体评价,梁光正是中国的堂吉诃德式人物。
他身上这种理想化的正义感和乐观精神,酿成了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
在梁鸿看来:“白衬衫是一种象征,他是一个对自我有更高要求的人。
想超越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为一个更高意义的人。”
作家李佩甫感慨,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和意识上,超越了余华的小说《活着》。
《活着》是写人生的绝望。
而《梁光正的光》写的是低处的光,在尘埃里,在最低贱处发出的光,超越了绝望。
大时代破碎进了一家人的恩怨情仇
除了白衬衫,梁光正和父亲的性格也很相似,在困难面前都会幽默一把。
梁光正每次踌躇满志地开始他的经济计划: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总是那样幽默、乐观。
不把困难当成多么大的事情,继续兴致勃勃地开始盘算下一个计划。
这种幽默乐观,在梁鸿身上也能找到。
在访谈中,梁鸿时常会发出的一连串“哈哈哈”的笑声,眼睛弯弯的。
采访空隙,她也会主动和我们聊天。
但在少年时代,她的性格“比较封闭、边缘,处在一种自我漫游的状态”。
这与家庭环境和时代背景脱不开关系。
戏如人生,父亲天天唱的戏文,宛如一家人的真实写照。
在家里兄妹六人中,梁鸿排行老五。
她6岁那年,母亲得了脑血栓。
有一天,她正趴在小桌子上写字,就看到母亲躺在担架上被抬回来了。
“一村庄的人都跟在后面看热闹,眼神里充满对我的怜悯和难以形容的轻视。”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每年近千元的医疗费把这个农村家庭拽入了贫穷的深渊。
“母亲躺在那里,虚弱、枯瘦、僵硬。
她的面容被疾病侵蚀得扭曲变形。每一天都是灰色的,每一天都在叠加难以言喻的黑暗。”
初三那年,母亲去世了。
为了还债养家,父亲常年在外奔忙,总是会忽略了这个“爱哭的老五”。
没有人陪伴,梁鸿学会了和自己相处。
她偶尔逃学,一个人跑到梁庄后的湍水边发呆,看着野鸭在水中嬉戏,划过一道道弧线。
闻着紫丁花沁人心脾的香气……
大家庭里的亲情关系,从来都很复杂。
每个人都想被爱,又怕被伤害。
梁鸿说:“我自己接近书中梁光正的两个女儿冬玉和冬竹的结合体。
比较懦弱,希望家庭好,但又没什么办法。”
母亲不在,长女如母。
梁光正的大女儿冬雪是个操心的命,梁光正一不安分。
她就得理不饶人地用连珠炮似的语言抨击他。
冬雪最爱父亲,最希望这个家好,但却用错了方式,一家人的心反而离得更远。
长子勇智与梁光正之间一直是反讽的、紧张的关系。
勇智很聪明,喜欢分析,能看透梁光正身上的矛盾性,及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意义。
所以他始终对父亲有敬畏,当然也有不满。
梁光正临终前,冬雪不断给勇智打电话,让他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勇智却没有回去。
在梁光正的葬礼上,他的棺木迟迟无法顺利落入墓坑。
儿子勇智和继子小峰先后跳到墓坑里抬棺安放父亲。
看到父亲入土为安,永远离开了自己。
一瞬间,他们的情感再也无法抑制,像洪水般汹涌而出。
勇智、小峰和冬玉三兄妹,跪在墓坑边缘,互相抱着一起磕头痛哭。
一直到死,梁光正依然在用他的意志指挥子女行动,让他们劲往一处使,心拧成一股绳。
这时候,子女们才对父亲有了一点点理解。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梁光正一家,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典型的中国式家族。
大多出生在六七十年代。
那个年代,一家人都是穷过来的,父母总共挣一百多块钱,把兄妹五六个拉扯大。
“但是兄妹之间,以及他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那个戏可大了,爱恨情仇、相互伤害、相互纠缠但又永远撕扯不开。”
梁鸿对中国的亲情关系有着长期的关注。
她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
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
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
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
可是,每当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
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
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中国的父子、父女、夫妻之间,永远是暧昧的、若即若离的关系。
即使爱也不能充分表达,恨也不是完全的恨。
在爱怨之间不断地游离,相爱相杀,最后搅出来这样一种深刻的血肉关系。”
“到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
父亲身上乐观的、幽默的、对生活会心一笑勇敢承受的心态,在我身上也慢慢地体现出来了。”
采访时,摄影师需要拍摄梁鸿的一些外景镜头,我们来到了人民大学图书馆附近取景。
隔着很远的距离,我都能听见梁鸿时不时发出的笑声。
说话时偶尔还伴有河南方言向上扬的尾音,在冬日萧索的空气中,绽放出一丝热闹和暖意。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经过这么多年,梁鸿慢慢发现,自己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头,越来越像父亲了。
“我们那叫‘头别着’,总在想自己的事情。”
1991年,18岁的梁鸿从河南穰县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里的一个乡当小学老师。
其他师范的同学都在老老实实地教书。
可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不能就此停滞,“想要做一些格外的事情”。
她一直坚持读书,考进了教师进修学校。
“很多人来进修就是为了一个文凭,没有人认真学习。
每天下午和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教室里学习,但过得非常充实,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她并不满足,又接连上了脱产大专,自学本科。
后来考上了郑州大学的硕士和北师大的博士,清一色报的都是中文系。
2003年博士毕业后,梁鸿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成为了批评家、学者。
写的都是纯粹的专业论文、论述。
虽然研究做得很顺利,但她渐渐产生了一种很强的空虚感,觉得自己离现实和生活越来越远。
“人被局限在专业之内,突破不了那堵看不见的墙,也进不到自己的内心。”
带着困顿,2008年夏天,她回到家乡梁庄,前后住了五个月。
这段时间,她观察了乡亲、村庄的变化,发现了种种现实问题,想写下梁庄的故事。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做研究和搞创作之间存在较深的隔阂,要冒很大的风险。
梁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全家人庄严、安静地听她讲计划,都觉得这是件正经的好事儿。
父亲说,你不会“扯秧子”(拉家常),得我陪。
在父亲生命的后期,他陪着梁鸿,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
去往二十几个城市,行走在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
“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
父亲比我还着急我的新书,躺在病床上时,还给我电话催我赶紧把书出出来”。
在采访梁庄的过程中,梁鸿才更加深入地认识了父亲。
2015年,梁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也是这一年,父亲去世了。
梁鸿眼前时时浮现父亲乐观自嘲和孩童般的无畏形象,不把他写出来,她寝食难安。
从创作非虚构作品到写小说,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一直以来,中国乡土文学受鲁迅影响颇深。
描述的农民形象大多是愚昧落后、冷漠麻木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物已经深入人心。
写《梁光正的光》时,梁鸿一开始按照固有的习惯写作。
写出来一读,她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跳脱鲁迅的思想框架。
她推倒重来,看了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的书。
还研究了很多小众作家的作品,一边学习,一边排除。
她抛弃了学术腔调,采用生活化、乡土味儿的语言,用高度戏剧化的手法。
写出了梁光正的故事。
“如果我没那么倔犟、那么坚持,《梁光正的光》可能我也写不出来。
也写不出来梁光正这样一个人物。”
即使写了十几万字后,梁鸿还是没有完全了解父亲。
“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辈。
他们的经历也许我们未曾经历,但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所遭受的苦,所昭示的人性。
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
有网友在豆瓣上说,读完这本书,想起一个自己憎恨过的亲人,现在要好好想想他。
很多人和梁鸿说,她做了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界限,总是在越轨。在别人看来是勇敢,其实还是因为比较单纯。
我的越轨实际上来自于本性,来自于生命本能,这点和梁光正是有点像的。”
写作,对梁鸿来说,是一次次对自我的挑战,是一个个学习的过程。
“我广泛吸收新的东西,再融会贯通。
慢慢形成自己生命和思想的底色,也许有一天,就会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从乡村教师,到人民大学教授。
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光正的光》。
梁鸿倔强而乐观地面对人生,听从内心的声音,探索未知的远方。
也许道路慢阻且长,但创作不会停止。
背景音乐-《天之痕》(钢琴版)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